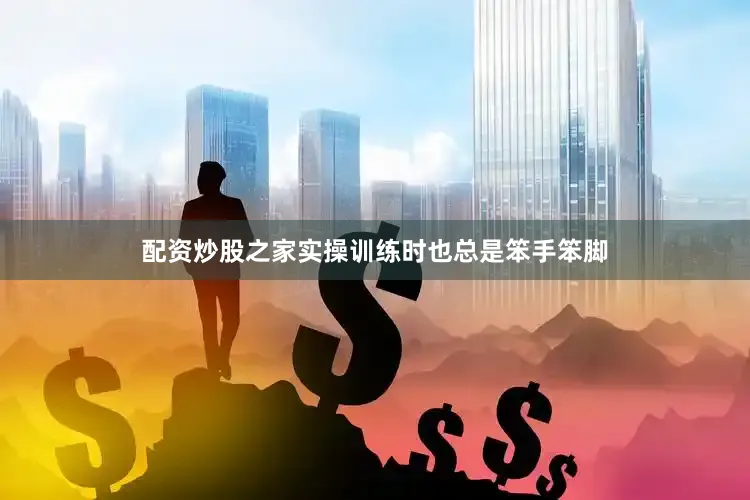天风浩荡,吹落人间数十年。当龚自珍“天风吹我”的诗吟嵌入作家黄济人八十载的生命纹理,便化作一柄青铜古剑,劈开生活迷雾,发出直抵人心的锐响。黄济人自传体长篇小说《天风吹我》,共21.6万字,近日由重庆出版社出版。作品横跨半世纪之久,在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中展现出中国当代社会的波澜壮阔之变。其人生如树,扎根巴渝山地的粗粝与风霜中,散发着三峡浪涛的咸腥与浩渺之气。
《天风吹我》的“风”,绝非轻柔拂面的微风,而是裹挟着强大力量的罡风。那是能掀翻茅草屋、冻裂板车铁轴的狂风,更是裹挟着百万移民血泪与汗水的江风。书中,作家那国民党投诚将领的家庭背景,曾如一块沉重巨石,自幼便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身份的束缚如影随形。青年时期,他被中学拒之门外,求学之路被生生阻断。然而,生活的重压并未使他沉沦,反而淬炼出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。为了生存,“皮肉之苦也许算不了什么”,他拉过板车,在长达半年的苦力生涯里艰难谋生,脊梁骨咯吱作响。面对磨难,他咬牙熬。他坚信,熬过漫漫长夜,终会迎来黎明曙光;熬过绵绵雨季,定能重见雨后晴空。这份坚韧恰似深埋地下的种子,在艰苦岁月里默默蓄势,最终点燃了他心中永不熄灭的文学之火。
展开剩余77%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,为作者带来命运的转折点,也让他笔下的世界更为广阔。他以笔为剑,直面时代风云,展现出无畏的勇气与担当。在创作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时,尽管作品题材和故事均涉特殊的人特殊的事,但他心怀孤勇,四处奔走采访,不放过任何真相细节。每一次采访都是一场挑战,他遭遇过拒绝、碰壁,却从未轻言放弃。他遍访战场老兵,亲访历史老人,聆听他们的浴血往事,记录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,最终凝聚成震撼人心的作品,成为重庆这座城市的文化地标。
三峡工程的背后,是百万移民命运的巨变。在记录这一宏伟壮举时,作家更显执着与担当。他足迹遍布11个省市,深入移民群体,躬身倾听移民浪潮中的个体命运。他亲历开县移民迁居广东肇庆,记录他们努力学习当地口音,却仍“像贵州骡子装马叫”般蹩脚,见证了“方言不通,连牛都听不懂‘人话’”的窘境。然而,面对异乡的重重挑战,移民们从未被击垮。凭借着泪水、汗水、牺牲与奉献,他们最终在新的土地上扎根,适应了全新的生活。作家将这些浪潮里的草根故事,铭刻进文字,用《命运的迁徙》这部报告文学,为三峡移民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,作出了最生动、最深刻的注脚。
《天风吹我》中,作家亦触及了重庆直辖这一重大历史节点。直辖,不仅意味着城市的宏图腾飞,于黄济人而言,更是时代赋予他的全新使命。身为全国人大代表,他积极推动社会发展进程。他深入基层,躬身体察民众的切身需求,汇集社情民意,积极建言献策。最终,他通过《一个人大代表的日记》,为民鼓与呼,将党与民众的声音传扬开来,这是他作为一名文人,所践行并书写下的时代责任与社会担当。
《天风吹我》最惊心动魄之处,在于将宏大叙事拆解成“血肉模糊”的碎片,再用文人的良知重新缝合。你能看见移民的耕牛对着异乡方言发愣,像被时代甩出轨道的符号;你能听见世仇家族在移民船上互道“好生将息”,方知生存面前什么深仇大恨也会骤然矮化半截。作家用自己一生的亲历,站立时代缝隙间,左手握剑,解剖时代和人性的真相;右手持箫,温柔抚慰个体命运的伤痕。凛冽与温情在他的文字中殊死搏斗,以剑之犀利、箫之柔情,细腻地描绘出对家国社稷的深沉情感,对亲友故旧的无限爱意,以及对人世间美好事物的由衷赞美。
他勾勒母亲“树挪死,人挪活”的生存哲学,描绘大姐于歧视中撑起的生活微光,也有自己躲在蚊帐里、借手电筒草拟书稿的倔强剪影……个体的微弱之光,只要未曾熄灭,便能汇聚成照亮历史的熊熊火炬。当三峡江水漫灌古老城池,他用笔在水底构筑起精神之城。那些因移民而即将沉没的笑声、哭声、吆喝声,都被他一一挽留。正如他所记录的云阳两户世代为敌,曾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,却在移民轮船上不期而遇时,能互道出“个人在外头,要好生将息呵”的温情关怀。这种人性转向的温暖,构成了其作品最为动人的灵魂篇章。
黄济人说,他记事很晚,懂事很早。他像一位守夜人,更像一位燃灯者。他不仅见证了不同生活形态的变迁,更深谙苦难岁月里的如何坚守。他用冷峻的笔触,剖析特殊年代的历史人物与事件,倾诉人性的挣扎、光辉与黑暗,从而彰显尊严与人性之光。笔下人物无不鲜活真实:无论是远赴万源教书,于贫困与身份歧视夹击下依然坚韧不拔的大姐,抑或面对家庭动荡却始终保持善良坚强的母亲,都栩栩如生。
因此,“天”是碾压一切的时代巨轮,“我”是轮下倔强生长的野草。“天”是大时代的转折与进步,“我”则是时代洪流中的渺茫个体。作家在《天风吹我》中最称道之处,在于他能让“我”这株微弱的野草,于巨轮碾压之下,依旧能挣扎着抽出新芽。他书写苦难,却不贩卖苦难;他描摹伤痕,却不沉溺伤痕。字里行间,始终奔涌着“熬过天黑即是天明”的强悍生命力。这份力量,使得那些隐藏在历史阴影里的沉疴无所遁形,亦使那些深藏人性中的光辉愈发璀璨。
他记录从乡村老人到工厂工人,从战后青年到改革知识分子……一个个故事,既是独特的个体历程,亦是时代的微观缩影。其细腻的笔触,彰显了对人性的深邃洞察,更展现了坚守底线、尊重生命的核心价值观。即便步入晚年,他仍笔耕不辍,深挖苦难,反思荒诞与美好,用文字为逝去的岁月留下珍贵记忆。
合上书页,眼前不断涌现出他抚摸曾经居住过的茅草屋土墙和柴门的场景,仿佛天风在耳畔呼啸。风里有板车碾过石子的钝响,有移民登船时的呜咽,有笔尖划过纸面的锐鸣。作家站在风中,白发猎猎,他说:“真正的文人不是时代的旁观者,是在狂风中有不肯折断的骨头。”无论是谁,即使身处黑暗,也要相信光明;即便环境艰难,也要坚定信念。只有解放全人类,才能解放自己。当所有喧嚣散去,那些不肯折断的骨头,在天风裂帛处,自有骨成碑——或许,这便是《天风吹我》留下的滚烫回响。
《天风吹我》不仅是一部自传,更是一张时代精神图谱。书中“天”与“我”完美统一,以个人叙事折射民族记忆,用笔墨耕耘呼应时代变迁,恰是中国文学“文以载道、史以鉴今”传统的生动延续。正如黄济人在电影《芬芳誓言》中“黄济人饰演黄济人”一样,这本书也展现出“怨去吹箫,狂来说剑,两样销魂味”(龚自珍《湘月·天风吹我》)的独特魅力,必将激励后来者用坚韧、勇气与责任感,书写出更多属于“我”的时代篇章。
启泰网-配资公司资讯门户网站-如何开杠杆炒股-配资炒股交易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